来源:天天新报 2012年2月29日 A02版
标题:陈永明:杰出人才培养需要创新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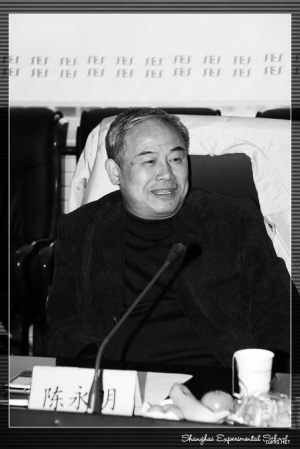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答案。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很难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我们的教育该如何更好地在传承的同时,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完美体育365WM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日前接受记者专访,给出了他的意见。○新报记者 茅中元
【人物名片·陈永明】
完美体育365WM教师教育学科群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主任、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茨城友好联谊会会长、“中国在日学人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在日期间,成立“中国在日学人教育研究会”(担任会长),组织100多名留学人员为国家有关方面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荣获“上海市回国留学人员先进个人”的称号。主持国家和上海市研究课题15项,负责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小学校长队伍建设的调研以及参与教育部“2020年教育发展纲要”(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专家组成员)的研讨工作。
东方文化适宜
培养标准化人才
新报记者:东方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人才教育、培养的理念和模式,存在怎样的差异?
陈永明: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代际传承,教育与文化有着非常深的姻缘连带关系,它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文化进程。
古希腊的教育哲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说”——西方的老师带领学生追求真理的时候,是以探讨问题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去辩论、推理,让学生在辩论、推理、思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来看东方文化的象征,《论语》、《道德经》都是采用权威式传授方法,把其核心思想和内容灌输给学生,重视自上而下的教化。
我曾把西方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有过一个归类,如果西方文化的特征可以视为“十字架文化”,讲究的就是拓展和推演;那东方文化的特征是“圆形文化”,偏重向心力和凝聚力。
西方文化从小让孩子亲近自然,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去探险,就是培养孩子从小要有一种探险、发现、分析的本领;而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重视的是安居乐业,我们所希望的是有一个礼仪来保证生存环境的有序安定。所谓“礼”就是社会的秩序,要有一个权威,所以诞生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有它的信条,有它教化的方法,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儒家有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但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孟子倡导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公元606年开始科举制度后,我们的教育就跟英才选拔联系在一起了。当时设立这种制度,是先进的、革命的,摒弃了世俗观,平民子弟十年寒窗也可以跳龙门,所以当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科举可以说是从制度上保证、强化了东方文化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和求同性的作用,再加上这种考试制度逐步被统治者禁锢之后,就变成最适宜培养标准化人才的通道。
新报记者:您说的标准化人才是怎样的人才?
陈永明:所谓标准化,就是当权者所喜欢的人才。学、注《四书五经》,必须通过乡试、县试、省试,最后到皇帝殿前钦点的状元,这才是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正宗人才。实际上老百姓也有这种科举文化的情结或偏爱,认为只有通过考试出来的人才,才是值得认可的人才。
“考试价值观”阻碍
“杰出人才”的培养
新报记者:钱学森有个著名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您觉得也和科举文化有关?
陈永明:我觉得并不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老师不想进行改革,如果人们心中的科举文化情结没变,整个社会的教育就会被绑在科举文化的“战车”上,你没办法跳下来,当社会各界对一个孩子的认可都是根据考试成绩来判断的话,你让我们的学校怎么改?
现在的家长都希望孩子不能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于是从幼儿园开始就看应考准备或条件的好坏。进了学校,比的就是成绩,现在又都是独生子女,谁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比邻居家的差,这样就变成了一种单向的、以成绩作为唯一或主要的评价标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就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中国人考试是一流的,我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考试全都是A。可其他国家的学生不太在意考试成绩,注重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尤其是理工科,我国留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成绩很好,到三年级一进实验室,差距马上就出来了。人家一进实验室,有的没等老师讲就开始动手了,而中国学生往往是先要听话,规规矩矩等老师讲,因为从小就要循规蹈矩,不然就不是好学生了。
新报记者:大家都说应试教育很不好,但把它去掉的话,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可以替代?
陈永明:我不是说考试不好,科举考试也有合理性、科学性的方面。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是学发达国家的,而最早进行公务员考试的英国,就是学了我们的科举考试。通过国家的公开考试,给人们转变社会身份的机会,这种方式在那个年代看,是有其合理性和公正性的。只是选拔的方法应当与时俱进。
新报记者:怎么样才算杰出人才?
陈永明:我想,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肯定有一部分是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创新人才,能够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可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人才很少。老祖宗有四大发明,我们在农耕时代能够有这样的发明,很了不起。但很可惜,进入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直到今天,我们能被世界认可的发明在哪里?这个结果我觉得跟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紧密相连,我们培养的是不敢挑战权威的人,所以学生不可能会去异想天开,更没法有能使自己的创新意识和精神自由飞翔的空间,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这样一种时间和空间。
新报记者:造成这个困局的原因是什么?
陈永明: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家庭环境,我们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一点也不宽容,现在的孩子活得很累,我这里可以举一个日本老师布置假期作业的例子。那是我女儿在日本读小学时放暑假,老师没有布置任何作业,也没规定必须干什么,就说每个人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记录下来,开学后公开展示。我女儿就种一棵植物,每天浇水,看植物的生长进度。在新学期的家长参观公开课时,有的学生是每天观察星空的日记和照片,还有的是同父母去旅游的感想文章和摄影介绍等等。这就是利用假期,让孩子们有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挥自己的潜能智慧。而我们的嫩苗,还没有出生就给往一个方向去拔,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自主独立发展方面比较欠缺。
新报记者:国内有这么一个说法——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中小学阶段让学生玩,边玩边找自己的兴趣,到了大学就朝着自己的兴趣去学。我们的教育是从小就苦学,到了大学开始放肆地玩。您认同这种现状吗?
陈永明:我们中小学的评价标准都是按大人要求来定的,大人要你考高分,自然不放心放你去玩,要给你定好了规矩,看你老老实实地学习,最后考个高分进好的大学。进了大学,仍和中小学一样灌输知识。学生十年寒窗出来,你又要学生这样被灌输好几年,他能感兴趣么。国外的中小学教育是让学生亲近自然,从自然中寻找自己的兴趣,到了大学他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深究苦学;而我们的学生从小是被动灌输知识,有了自主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
我们大学教育的水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老师讲的东西,有不少是学生不感兴趣的。好的老师,像易中天、于丹他们上课肯定爆满,其他的课为什么是能逃就逃?因为教育方式与内容太枯燥。
大学是一个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的重要场所。老师应该跟学生一起探讨、分析、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这样的老师不多。这和高校的考核也有关系,对老师的考核就是学生的出勤率和成绩、课时量以及科研业绩。这样会让老师只是想到怎么保证学生来上课,而不是怎么跟学生讨论问题。于是,很多学生只求考试及格,最后就业人家也就是看这张成绩单。其实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也是被成绩逼着学。
教育者要懂得
“丛林法则”
新报记者:我们如何看待校长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陈永明:现在中国的教师有1400多万,教师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校长。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美国、英国一些发达国家都有校长的专业标准,而我国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中小学校长标准。在上海曾有过一个调查,两个不同区的校长,在学历和学识方面都有很大的反差。这样就导致校长队伍的参差不齐。
在办学方面,我们又要求学校有它的特色,老师要有专业性、积极性、主动性。这些都需要校长来引导。我觉得全国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应该既有硬性标准,又有柔性指标。
新报记者:您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这个标准?
陈永明:在一次校长高峰论坛上,一位欧洲的校长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我们的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是进211、985高等学府的录取率。不仅是校长,还有教育局长、家长,都是这么关心的。曾经有一个教育局的局长非常认同我的学术观点:不该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但是必须得保证可以100%成功,因为中国人对应试成绩相当重视,即使1%的失败,都会否定99%的成功。
新报记者:要突破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陈永明:200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日本筑波大学校长江崎玲於奈先生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他讲演中有两句话让人很受启发。他说,他在美国实验室看到过这样一句名言:“偶尔偏离正轨,钻进丛林,你会得到惊人的发现。我和许多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投机家、冒险家一样,我们都偏离了正轨钻进了丛林,有的人堕落了,有的人迷茫了,可是我一直不断地开拓,不断地耕耘,我有了新的发现创造,我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你真正要搞创新教育,应当从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开始,给孩子有一个宽松愉快的、自由自主自律的环境,他们潜在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兴趣爱好和开拓精神就能发挥出来,中国明天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也许就会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出现,包括钱学森说的杰出人才。
他的第二句话是:“每个人都有两种思维,一种是白天的思维,还有一种是黑夜的思维,白天就是逻辑性思维,黑夜就是想象性思维。”我们的教育现在过多注重白天逻辑性思维的培养,而忽视夜晚想象性思维。放学回家布置很多的家庭作业,做好了以后家教来了,之后还有那么多的教辅资料。孩子的想象性思维空间都被大人剥夺了,久经考验炼成顺从统一的标准产品,很难成为异想天开的、创新进取的、翱翔在天空当中的经世济用之才,这也是中国时至今日在自然科学领域没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的教育也有不能够改变以及必须坚守的东西。不能够改变的是教育应当重视每个人的人格养成、人格陶冶。同时,作为家长,我们要教给孩子,生活在人类社会不能够忘记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不能够失去的是什么?那就是爱,爱这个地球,爱和你一起生活的植物、动物和他人,这些就是我们进入21世纪“学会共生”教育之根本。
标题:陈永明:杰出人才培养需要创新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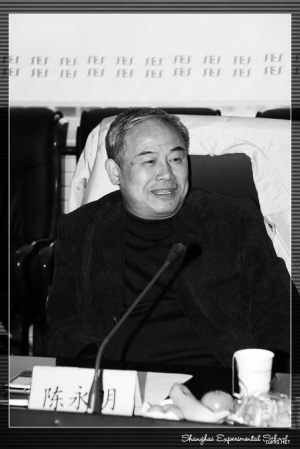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答案。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很难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我们的教育该如何更好地在传承的同时,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完美体育365WM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日前接受记者专访,给出了他的意见。○新报记者 茅中元
【人物名片·陈永明】
完美体育365WM教师教育学科群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主任、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茨城友好联谊会会长、“中国在日学人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在日期间,成立“中国在日学人教育研究会”(担任会长),组织100多名留学人员为国家有关方面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荣获“上海市回国留学人员先进个人”的称号。主持国家和上海市研究课题15项,负责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小学校长队伍建设的调研以及参与教育部“2020年教育发展纲要”(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专家组成员)的研讨工作。
东方文化适宜
培养标准化人才
新报记者:东方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人才教育、培养的理念和模式,存在怎样的差异?
陈永明: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代际传承,教育与文化有着非常深的姻缘连带关系,它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文化进程。
古希腊的教育哲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说”——西方的老师带领学生追求真理的时候,是以探讨问题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去辩论、推理,让学生在辩论、推理、思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来看东方文化的象征,《论语》、《道德经》都是采用权威式传授方法,把其核心思想和内容灌输给学生,重视自上而下的教化。
我曾把西方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有过一个归类,如果西方文化的特征可以视为“十字架文化”,讲究的就是拓展和推演;那东方文化的特征是“圆形文化”,偏重向心力和凝聚力。
西方文化从小让孩子亲近自然,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去探险,就是培养孩子从小要有一种探险、发现、分析的本领;而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重视的是安居乐业,我们所希望的是有一个礼仪来保证生存环境的有序安定。所谓“礼”就是社会的秩序,要有一个权威,所以诞生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有它的信条,有它教化的方法,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儒家有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但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孟子倡导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公元606年开始科举制度后,我们的教育就跟英才选拔联系在一起了。当时设立这种制度,是先进的、革命的,摒弃了世俗观,平民子弟十年寒窗也可以跳龙门,所以当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科举可以说是从制度上保证、强化了东方文化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和求同性的作用,再加上这种考试制度逐步被统治者禁锢之后,就变成最适宜培养标准化人才的通道。
新报记者:您说的标准化人才是怎样的人才?
陈永明:所谓标准化,就是当权者所喜欢的人才。学、注《四书五经》,必须通过乡试、县试、省试,最后到皇帝殿前钦点的状元,这才是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正宗人才。实际上老百姓也有这种科举文化的情结或偏爱,认为只有通过考试出来的人才,才是值得认可的人才。
“考试价值观”阻碍
“杰出人才”的培养
新报记者:钱学森有个著名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您觉得也和科举文化有关?
陈永明:我觉得并不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老师不想进行改革,如果人们心中的科举文化情结没变,整个社会的教育就会被绑在科举文化的“战车”上,你没办法跳下来,当社会各界对一个孩子的认可都是根据考试成绩来判断的话,你让我们的学校怎么改?
现在的家长都希望孩子不能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于是从幼儿园开始就看应考准备或条件的好坏。进了学校,比的就是成绩,现在又都是独生子女,谁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比邻居家的差,这样就变成了一种单向的、以成绩作为唯一或主要的评价标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就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中国人考试是一流的,我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考试全都是A。可其他国家的学生不太在意考试成绩,注重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尤其是理工科,我国留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成绩很好,到三年级一进实验室,差距马上就出来了。人家一进实验室,有的没等老师讲就开始动手了,而中国学生往往是先要听话,规规矩矩等老师讲,因为从小就要循规蹈矩,不然就不是好学生了。
新报记者:大家都说应试教育很不好,但把它去掉的话,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可以替代?
陈永明:我不是说考试不好,科举考试也有合理性、科学性的方面。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是学发达国家的,而最早进行公务员考试的英国,就是学了我们的科举考试。通过国家的公开考试,给人们转变社会身份的机会,这种方式在那个年代看,是有其合理性和公正性的。只是选拔的方法应当与时俱进。
新报记者:怎么样才算杰出人才?
陈永明:我想,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肯定有一部分是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创新人才,能够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可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人才很少。老祖宗有四大发明,我们在农耕时代能够有这样的发明,很了不起。但很可惜,进入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直到今天,我们能被世界认可的发明在哪里?这个结果我觉得跟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紧密相连,我们培养的是不敢挑战权威的人,所以学生不可能会去异想天开,更没法有能使自己的创新意识和精神自由飞翔的空间,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这样一种时间和空间。
新报记者:造成这个困局的原因是什么?
陈永明: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家庭环境,我们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一点也不宽容,现在的孩子活得很累,我这里可以举一个日本老师布置假期作业的例子。那是我女儿在日本读小学时放暑假,老师没有布置任何作业,也没规定必须干什么,就说每个人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记录下来,开学后公开展示。我女儿就种一棵植物,每天浇水,看植物的生长进度。在新学期的家长参观公开课时,有的学生是每天观察星空的日记和照片,还有的是同父母去旅游的感想文章和摄影介绍等等。这就是利用假期,让孩子们有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挥自己的潜能智慧。而我们的嫩苗,还没有出生就给往一个方向去拔,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自主独立发展方面比较欠缺。
新报记者:国内有这么一个说法——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中小学阶段让学生玩,边玩边找自己的兴趣,到了大学就朝着自己的兴趣去学。我们的教育是从小就苦学,到了大学开始放肆地玩。您认同这种现状吗?
陈永明:我们中小学的评价标准都是按大人要求来定的,大人要你考高分,自然不放心放你去玩,要给你定好了规矩,看你老老实实地学习,最后考个高分进好的大学。进了大学,仍和中小学一样灌输知识。学生十年寒窗出来,你又要学生这样被灌输好几年,他能感兴趣么。国外的中小学教育是让学生亲近自然,从自然中寻找自己的兴趣,到了大学他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深究苦学;而我们的学生从小是被动灌输知识,有了自主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
我们大学教育的水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老师讲的东西,有不少是学生不感兴趣的。好的老师,像易中天、于丹他们上课肯定爆满,其他的课为什么是能逃就逃?因为教育方式与内容太枯燥。
大学是一个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的重要场所。老师应该跟学生一起探讨、分析、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这样的老师不多。这和高校的考核也有关系,对老师的考核就是学生的出勤率和成绩、课时量以及科研业绩。这样会让老师只是想到怎么保证学生来上课,而不是怎么跟学生讨论问题。于是,很多学生只求考试及格,最后就业人家也就是看这张成绩单。其实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也是被成绩逼着学。
教育者要懂得
“丛林法则”
新报记者:我们如何看待校长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陈永明:现在中国的教师有1400多万,教师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校长。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美国、英国一些发达国家都有校长的专业标准,而我国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中小学校长标准。在上海曾有过一个调查,两个不同区的校长,在学历和学识方面都有很大的反差。这样就导致校长队伍的参差不齐。
在办学方面,我们又要求学校有它的特色,老师要有专业性、积极性、主动性。这些都需要校长来引导。我觉得全国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应该既有硬性标准,又有柔性指标。
新报记者:您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这个标准?
陈永明:在一次校长高峰论坛上,一位欧洲的校长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我们的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是进211、985高等学府的录取率。不仅是校长,还有教育局长、家长,都是这么关心的。曾经有一个教育局的局长非常认同我的学术观点:不该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但是必须得保证可以100%成功,因为中国人对应试成绩相当重视,即使1%的失败,都会否定99%的成功。
新报记者:要突破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陈永明:200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日本筑波大学校长江崎玲於奈先生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他讲演中有两句话让人很受启发。他说,他在美国实验室看到过这样一句名言:“偶尔偏离正轨,钻进丛林,你会得到惊人的发现。我和许多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投机家、冒险家一样,我们都偏离了正轨钻进了丛林,有的人堕落了,有的人迷茫了,可是我一直不断地开拓,不断地耕耘,我有了新的发现创造,我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你真正要搞创新教育,应当从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开始,给孩子有一个宽松愉快的、自由自主自律的环境,他们潜在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兴趣爱好和开拓精神就能发挥出来,中国明天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也许就会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出现,包括钱学森说的杰出人才。
他的第二句话是:“每个人都有两种思维,一种是白天的思维,还有一种是黑夜的思维,白天就是逻辑性思维,黑夜就是想象性思维。”我们的教育现在过多注重白天逻辑性思维的培养,而忽视夜晚想象性思维。放学回家布置很多的家庭作业,做好了以后家教来了,之后还有那么多的教辅资料。孩子的想象性思维空间都被大人剥夺了,久经考验炼成顺从统一的标准产品,很难成为异想天开的、创新进取的、翱翔在天空当中的经世济用之才,这也是中国时至今日在自然科学领域没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的教育也有不能够改变以及必须坚守的东西。不能够改变的是教育应当重视每个人的人格养成、人格陶冶。同时,作为家长,我们要教给孩子,生活在人类社会不能够忘记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不能够失去的是什么?那就是爱,爱这个地球,爱和你一起生活的植物、动物和他人,这些就是我们进入21世纪“学会共生”教育之根本。
热点新闻












 徐汇校区: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
徐汇校区: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